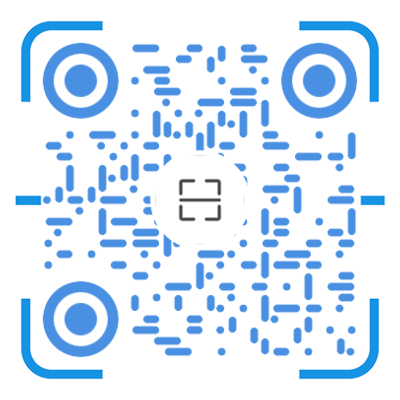发小陈江:在贫穷与喧嚣里长大,他终究成了自己最厌弃的模样
街坊们都说陈叔是厚道人,可在穷街陋巷里,“厚道” 往往是没本事的同义词,方便大家心安理得地从他身上踩过去。陈叔唯一的动静就是咳嗽,咳得惊天动地。有几次来我家买烟,我妈劝他少抽点,买点肉吃,他就笑笑,把腰带再扯紧些,说 “你们女人懂个啥”。我妈等他走远了就念叨:“他那嘴啊,还不如当个烟灰缸管用。”
陈江他妈刘姨,倒是出了名的能干。在菜场弄了个巴掌大的档口,卖廉价袜子、毛巾手套。那张嘴跟地摊货似的,利索又糙,能把一块钱掰成八块花。来我家买包盐,都要扯个最大的免费塑料袋,嬉皮笑脸的能把我妈磨得没脾气。可急了眼能追着顾客骂,那架势像是要咬人。
陈江的童年,始终绷得紧紧的。沉默和争吵,是穷人家最常见的语言。刘姨的抱怨像夏天的蚊子,无孔不入:“老陈你个没用的东西,躺着就剩一张嘴”“老陈你又抽烟,哪像个男人”。
很快,刘姨的叫骂变成了哀嚎哭泣 —— 陈叔为了证明自己是男人,把她拖到门口打。街坊们就站在一边劝劝,既怕伤着陈叔的腰被讹,又怕误伤到自己,毕竟陈家也没啥钱可赔。这压根就是陈叔在街坊面前找回尊严的表演赛,劝劝,不过是用道德换来的观赏券。
陈江就在这样的硝烟和死寂里长大。他随爹,扔人堆里都捞不出来,学习也就勉强混着,在学校就是个透明人。女生不看他,男生拉帮结派,他只能跟几个同样窝囊的同学跑腿、听人吹牛。不被异性善待,不被同性接纳,卑微的种子在见不着太阳的地方悄悄发了芽。
我那时实诚,以为她们真穷,从家里店里摸了些零食装书包里。她们见我有盒装薯片,眼睛都亮了。最好看的黄毛姐姐特礼貌地问:“我能拿走吗?” 我腼腆点头,她还热心帮我拉上书包拉链,送我走了好一段,说:“有我在没人敢欺负你,我保护你。”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动人的誓言。
可被她吼的人里,就有陈江。我快到家时,他跑来问我怎么认识那些大姐姐的。我小小年纪竟有点装逼,没说自己是被劫的,只说 “我请她吃零食了”。陈江瞬间被折服,说 “你家开店真好”。我见他若有所思,赶紧打断:“别别,你可别送袜子,那是神经病干的事。”
没多久,陈江干了件 “惊天动地” 的事。他存了一块钱,等了三天,买了根淀粉肠,径直走到一个短发太妹面前,摆出居高临下的脸递过去:“拿去,我请你。” 那表情是从他爸那学的,每次打完他妈后就那模样,他想把父亲的窝囊和暴力,化成雄性魅力泼给对方。
结果换来了一顿巴掌,那是小太妹们第一次联合出击,陈江很快被扇到墙角。那一刻我才知道,瘦得厉害的人,打肿脸也成不了胖子。
那天后,陈江两天没上学。第三天来学校,才发现自己的事迹被传得变了样,有人说他调戏女流氓,有人模仿他递烤串的嚣张表情,连年级小混混都拉他去小花园开会,就为了看他再演一遍。去厕所都有人拍他肩膀夸 “胆识过人”。
再往后,他真成了小混混的一员。遇见低年级的挡路,能直接吼开,没事窝在花园抽烟,腰杆挺起来了,走路却外八了,笨拙地复刻着小混混的雏形。
这不属于同龄人的话让我们惊讶。他接着说:“你们没接触社会,我常和大人玩,学到的多了去了。猫哥认识不?玩自行车的,有钱,女朋友特好看!算了,跟你们小屁孩说不懂。” 他抽了两口,把烟熄了装回兜里快步走开。我和同学等他走远,异口同声地夸:“真傻比。”
陈江见她不搭理,扭头冲远处吼 “萍萍”,没人应就起身回自己桌。没一会儿,他端着半盘牛肉过来,身后跟着个姐姐,拉着她坐下搂在怀里:“这我女朋友,在外头给我面子,我说一她不说二,这才是女人,这才是家教,晓得不?”
我女友笑嘻嘻地对那姐姐说:“你好倒霉哦。” 又发现锅里肉没了,骂:“哪个狗东西,吃得一点渣都不剩。” 我忙说再点,陈江舌头都喝大了,我赶紧叫服务员买单,怕一会儿伤和气。
那姐姐劝他:“回去吧,别打扰别人了。” 他扒拉开她的手:“我给他们讲道理,他们不懂。有钱才有尊严。”
最后我拉着女友赶紧走了,她挽着我胳膊说:“他和他女朋友,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,活该凑一对互相祸害,咱们可别学。”
前年,我和朋友在楼下吃宵夜,又碰见陈江,他点了炒饭打包,在我们桌坐了会儿。我问他结婚没,他摇头说 “好些年没谈恋爱了”。我说 “那会儿那个小姐姐呢”,他叹气:“早不联系了,人都现实。我那时候搞得还可以,算年少有为,现在就这样了。”
“所以后来你没钱,她甩了你?” 我问。“那倒不是,是我以为快有钱了,甩了她。” 他笑了笑。我说 “一个人也挺好”,他摇头:“不行,得结婚,主要得有后代,老祖宗的东西有道理。”
“那单着是因为啥?” 他掏出烟盒,抖出最后一根点上:“现在的女人和以前不一样,没钱不和你过。我算看透了,情啊爱啊都是假的,就得有钱。你看我爸,窝囊一辈子,不就是没钱?等我有钱了……”
店员喊 “打包好了”,陈江扔掉还剩大半截的烟,匆匆起身摆手:“走了。” 身影融进宵夜摊的喧嚣人流里。
他始终没明白,女人不和他过,可能和钱有关,但和他像不像他爸,关系更大。
他坐过的塑料凳旁,烟头明明灭灭,像被无数次掐灭的幻想,也像他父亲窗下永远燃不尽的廉价烟蒂。他们都在烟雾里,活成了对方最厌弃的样子,却坚信这是唯一正确的活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