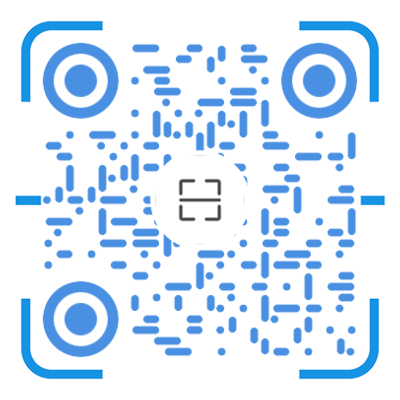院角那棵老槐树又落了叶,枯叶堆里埋着我童年的影子。那时总觉得父母的脊背是天底下最结实的墙,母亲在灶间揉面的手纹里藏着麦香,父亲蹲在门槛上敲烟锅的火星,能把暮色烫出窟窿。我们兄弟姐妹像槐树枝桠上窜出的新芽,争着往阳光里钻,却没看见树根在泥土里一寸寸皴裂 —— 他们把晨露酿成我们的奶水,把月光捻成我们的灯油,自己却在岁月里熬成了半截枯木。
记得某个夏夜里,蚊虫在煤油灯周围旋成雾,母亲的蒲扇摇出细碎的风,扇面掠过我胳膊时,能闻到她袖口沉淀的皂角香。父亲把我架在肩上走过田埂,北斗星在他头顶晃悠,他说:”你看那星星,爹娘就守在你走的每条路上。” 那时只觉得这话啰嗦,直到后来在异乡的霓虹里迷路,才忽然懂得,父母的目光原是拴在游子脚踝的长线,哪怕隔了万水千山,也能在风里听见线头颤动的声响。
去年清明回老屋,推开门时蛛网在梁上结了冰。堂屋墙上的全家福已经泛黄,母亲的笑容被蛀虫啃出了洞,父亲的中山装领口磨得发白。灶台上还摆着我儿时用的豁口瓷碗,碗底沉着经年的米垢,像沉在时光深处的叹息。忽然想起有年大雪封门,母亲把热炕头让给我,自己缩在灶房草堆里睡,天亮时我看见她鬓角的霜花,竟以为是落了头的梨花。
如今站在老槐树前,才发现它的躯干早被虫蛀空了,可春天仍会从皴裂的皮缝里挤出新绿。就像父母佝偻的背脊里,永远藏着给我们的暖。上次视频时母亲把手机举得老远,说怕我看见她新添的皱纹,父亲在一旁咳嗽着打岔:”忙就别回了,家里有我呢。” 可挂了电话,我分明看见他偷偷抹了眼眶。
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,风里有多少片叶子在飞,就有多少个游子在回头望。当有一天老槐树轰然倒下,当父母的坟头长满了我们儿时种的蒲公英,我们才会明白:所谓家,从来不是那间砖瓦砌的老屋,而是父母目光所及的地方。趁暮色还没漫过他们的眉骨,趁灶间的烟火还能映亮他们的笑,该把漂泊的脚步往回挪一挪了 —— 毕竟这世间最不能等的,是在父母膝下再撒一次娇,是让他们看见,当年那棵急着离巢的小树苗,如今已懂得把根须扎回他们的土壤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