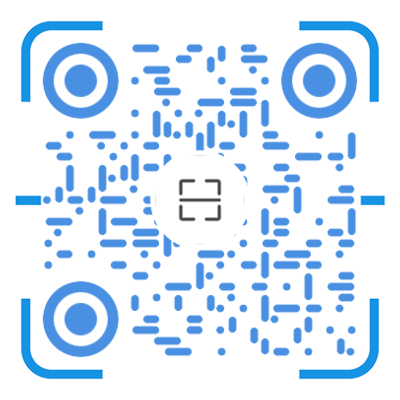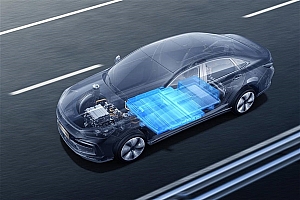存钱这件事,藏着我半生的印记
 身边总有人聊股票基金,那些 K 线图和收益率像天书,我从来插不上嘴。我不信什么 “躺赚” 的神话,更怕风险砸得人翻不了身,就想把手里的钱攥得紧紧的,一分一分存起来。普通人存钱,哪有容易的?背后都是过日子的掂量。
身边总有人聊股票基金,那些 K 线图和收益率像天书,我从来插不上嘴。我不信什么 “躺赚” 的神话,更怕风险砸得人翻不了身,就想把手里的钱攥得紧紧的,一分一分存起来。普通人存钱,哪有容易的?背后都是过日子的掂量。我打小从豫东一个穷村子里钻出来,爹娘是靠力气在城里讨生活的。家里重男轻女,姐妹好几个。2002 年前后,我 6 岁,爹娘一年到头挣的钱刚够糊嘴,连我上学的学费都凑不齐,只好把我送回河南老家。 现在想起来,村里环境差得没法说,可那会儿的我,从来没觉得苦。
大院子里挤着四间房,三间小瓦房加起来才 30 平,要住下爷爷奶奶和四个孩子。 东北角有间泥巴糊的厨房,门框矮得很,也就 1.6 米的样子。有天放学回家,看见满脸是灰的奶奶,还有正挨骂的爷爷 —— 咱家电饭锅的 “窝” 塌了半边。换现在,早拆了重盖,可那会儿,所有的人和物都在过一种缝缝补补的生活。 乡亲们搭把手,和着泥巴糊了又糊,新厨房很快又飘起了柴火香。
院子西南角那间,我实在不好意思叫它 “房”——三面半泥巴墙围出个露天旱厕,雨天解手得撑着伞,左手边堆着写完的作业本,那就是当时的厕纸。 小时候好些年都没见过卫生纸,现在都想不起来,那些日子是咋熬过来的。
那时候日子穷是穷,但简单。爷爷奶奶心里就一个念头:种地,能吃饱就行,钱嘛,能挣一点是一点。爹娘不一样,在城里打工,三顿饭都得算计着吃,满脑子想的是咋多挣点,让娃们有饭吃、有衣穿。“节约” 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消费信仰。 在这样的日子里长起来的我,自然也带着这股劲儿 —— 知足、会省,早就成了生活的一部分。研究生同学聊起小时候没买到漂亮连衣裙的遗憾,我的童年是在烂衣补丁中度过的。